现在抑郁低龄化趋势受到普遍关注,有学者认为现在的青少年普遍具有“弱现实感”,并由此引发诸多心理问题,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杜晓馨:《光明日报》旗下的《教育家》近日刊发了陈默老师的一篇文章,就谈到了“弱现实感”的问题,提到孩子们现在都感受不到现实生活的意义,因为生活都被安排好了,生活很被动,也常在虚拟世界获得感情体验。陈默老师认为这个和高焦虑的养育者,学习环境和高竞争的同伴关系等等,都是有关的。我一定程度上觉得这个现象确实存在,基本同意这种归纳。
杜晓馨:有段时间因为《他乡的童年》这部纪录片而看了不少讲芬兰教育的书,都会提到那里的孩子很快乐,有自己的兴趣,社会根本不强调竞争,认为职业和财富不能决定人的社会地位,但一个人看什么书,谈些什么,才是真正能赢得别人尊重的。看完以后,会让人忍不住反思,我们现在所身处的环境,整个社会的价值和芬兰差别还是挺大的。但同样在鼓励竞争的社会环境,其实大家都会面临很类似的问题。例如,我们智库的同事也为大家推介过美国学区房相关的研究报告;发展研究院也在媒体上分享过相关报告英国疫情之后,失业的状况使得年轻人出现了很多新心理上的问题。高竞争的社会会带来教育的功利化,在高校体现为学术资本化,在基础教育阶段比较明显的就是大家都会努力让自己的升学上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学区房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学生容易出现心理失衡也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事实上,从目前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这是高竞争社会所带来的比较普遍的问题。

《他乡的童年》纪录片海报
您认为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杜晓馨:要谈及原因,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些图景。首先,现在城市的孩子,离土地的距离就已经非常遥远了,农作物是怎么长出来的,怎么变成我们餐桌上的菜肴,其中经过了什么样的过程,孩子们会没有机会知道这些内容;再进一步说,在城市中生活的孩子,因为参与到的主要活动大多都与升学有密切的关系,从而导致他们可能甚至对于城市生活的运行规则也并不了解,银行是用来干什么的,共享单车为大家带来什么便利又可能有什么问题,在一切理所当然中被孩子们漠视了。孩子的生活缺乏了最基本的常识。
这其中可能有不同层次的行为者的责任。
就家长来说,对于孩子的生活规划完全围绕社会所产生的教育焦虑,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就从孩子的早期教育来说,很多家长都会把孩子送去早教机构,事实上所有机构背后的理念都是让孩子能够接触世界的不同方面,不同的人、不同质地的触觉、不同声音、不同动作的平衡感等等。然而事实上一个孩子在沙坑里,安安静静玩沙子的大半个小时,能感受到沙子从指尖流过,尝试去握住又被沙子逃走,尝试去塑形,尝试去倾倒,感受手指尖的神经被细软沙子刺激以后奇特的舒适感,所有的这些经历、体验其实都是孩子大脑形成思维的过程。但家长往往觉得这样随意玩沙子的一个小时是没有收获的,而在手机app里看到的孩子的课时量、生成的打卡图片才能让人安心。现在学龄前孩子在医院体检所使用的丹佛量表,从几个社交、精细动作、语言、大动作几个能区来给孩子一个全面的评价,事实上只是给家长一种参考,而家长对于孩子某一项目在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时间点上没有达标就会显得非常焦虑,事实上量表上的大部分项目,例如穿衣服、讲家长名字等等,都是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让孩子去学习并且学会的。但这些项目往往变成家长相互比较的一个指标,从而以量化的指标去规划孩子的生活,而忽视了孩童在玩乐的过程中得到的认知体验。
就学校来说,认知识记的内容确实相对过多,而实践的内容,探究社会运行的内容少了一些。我之前看过一些关于国外食育的文献,日本从2005年开始颁布《食育基本法》之后,将他们一直在学校进行的围绕食物的教育进行了立法化,他们的学校就在这个框架下开展了很多有意思的教育活动,以种植体验为代表的食育活动扩展到了学校的各个教学课程中,社会课主要讲述“粮食生产者”的相关知识,家庭课引导学生“自己准备早饭”,国语课则指导学生写作“活动报告”,道德课则以此为例讲授“生命的价值”,这和芬兰的现象教学有共通之处。这个是需要政策层面的鼓励的。
社会层面的原因比较复杂了,但总体看待这个问题的话,我个人建议大家可以看看熊易寒老师《平衡木上的中国》这本书或者相关的讨论中产阶级的文章。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经之路,我在香港求学的时候,就发现学龄前的中产的孩子,父母都在花很大的精力为孩子报名各种幼儿园名校,因为大部分这类学校都只有半天班,孩子一天要去两个学校,入学的报名费用就可能要用去几万,而不同层级的学校一环扣一环,你上了band 2的小学,很难上得了band 1的中学,那就逼着家长从幼儿园就开始疯狂择校,甚至为了后代的教育机会,将择偶变成一种投资。那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身边的环境,是否也有一些存在这样的倾向呢?确实有很多的家长生活在自己的孩子可能会阶层下滑的恐惧之中,这种恐惧再回过头来也确实就来源于高竞争的社会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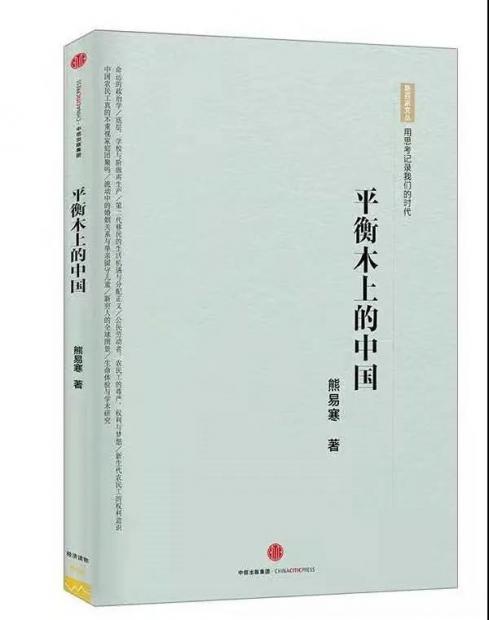
熊易寒《平衡木上的中国》
我国政府已经采取的措施有哪些?您认为在此过程中可以注意哪些问题?或者采取哪些措施吗?
杜晓馨: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家事实上已经开始重视相关的问题,今年国家在很多相关的层面都出台了文件,包括体育锻炼、劳动教育、美育、青少年近视问题、心理问题、青少年营养、社会实践等等方面。
在升学方面,国家也是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减负、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公民同招、地方的中考改革等等一系列的政策出台都是为了尽可能去促进一定程度上的教育公平,尽管对于个体家庭来说是折腾的,政策不停在变,但也要看到出发点上,是为了在更长的时间内,尽可能促成均衡的教育。
然而仅仅以政策是很难策动学校和家长的思维转变的,需要的还是整个社会对于什么样的人能够健康地生活在社会上,并力所能及地为社会做些贡献的整体思潮能有更加多元和宽容的态度,但这很难一蹴而就。
您之前提到家长的教育焦虑问题,在内卷的环境下家长自身也更容易产生焦虑的情绪和过度掌控,有些家长也直言缺乏陪伴时间,宁愿将孩子交给辅导班,而有些家长则会全身心投入孩子教育,精细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从家庭和个人的角度我们能做什么去减少焦虑,和进行“去弱现实感”?
杜晓馨:最近,同事分享给我的一篇文章在梳理几个海淀“鸡娃”号的相互关系网络,从该文之下的评论可以看出,这些相互关联的利益体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家长们的教育焦虑,他们在制造也在消费这种焦虑。所以还是不要一直看这些号了,把眼光放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多看他们纵向的个体的成长,而少做横向的比较,承认他们是独特的个体,接受他们的缺陷,看见他们身上的闪光点。
家庭和个人能够做到的还是我之前提到的,多多进行常识教育,让孩子能够清楚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和社会的链接。我曾经在朋友圈转发一篇文章,叫做《教育孩子就该带他们去菜市场》,我说这个意识很好,我有朋友批评我说这个说法太中产了,有些孩子就是生活在菜市场的。我觉得她说得没错。但今天如果我们去谈弱现实感的问题,可能确实更为聚焦在中产的孩子身上。那这些孩子应该多多去看菜市场,去帮大人算算钱,去想想今晚一餐如何能美味又营养,去看看菜市场卖菜的阿姨在看什么电视剧,去拜托大叔切一下刚买的排骨。家庭教育中多让孩子去参与家庭生活,甚至是家庭生活的一些决策。
杜晓馨:学校教育也要让政策文件不只是体现在纸面,或者仅仅只是完成任务。回想下我高中的时候也经历过学工和学农,但思忖再三我都觉得还是比较注重形式的,也许学农的内容放在学校大家一起找块小小的地种蔬菜会更有收获和成就感,也能体验到种植的全过程。如何真的能使得劳动教育帮助孩子和社会产生更加深厚的链接,是可以好好研究和设计的内容。

受访者简介
杜晓馨
杜晓馨,复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先后于2008年、201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获法学学士及硕士学位。2017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教育学专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2017年12月至2020年11月于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担任博士后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政策、学术人才流动、青年研究、高校中的政治社会化、公民教育。
注:本文为专访实录。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